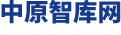“五四”的追叙与回响
———“‘五四’的反思与文化自觉”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05-02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作者:hnassadmin
点击量:2309
【字体:大 中 小】

会议以“五四”的反思与文化自觉为题,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自觉推动当代文化的建设与思考,目的在于让用力方向不同而各有建树的诸位学者在相对宽松的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流与碰撞,为每一种立场与态度开放空间,从而抵达更具深度的认知与理解。经过学者们热烈讨论,最终在“五四”的内涵与意义、“五四”的精神文化遗产、“五四”的研究与阐释,以及如何重新认识“五四”等议题上形成了较为集中的认识与看法。
“五四”内涵与意义。袁凯声研究员首先援引雅斯贝尔斯的概念,认为“五四”可视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轴心时代。“五四”不仅集中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且在此后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五四”提出的一些核心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仍然在当代中国发生影响,而后来者在承接、超越,甚至颠覆“五四”开创的传统时,依然还是在围绕着“五四”的精神探索和问题展开着。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与会学者的认同。关爱和教授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80年的发展历史,从器物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文化革命是符合历史梯度的一种升华,这个思想逻辑是符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历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层层深入,到“五四”时期真正进入到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出现所谓反传统的思想潮流。“五四”之后中国进入了文化转化和重建的艰难历史时期。经过90多年的转化与重建,基本的雏形已经建立,逐渐走到了文化的自信和历史的自信这样一个节点,形成了当下的文化支撑和文化理念。关教授强调,不同时代对“五四”的清理与反思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今天我们也不例外。十八大提出文化自信、自觉、自强的问题,其中涉及中国文化重建的两个重要基础是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没有爱国主义,可能国家会缺乏应有的民族团结和凝聚力,没有时代精神,可能会失去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关教授的发言立足于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以历史视野对“五四”的内涵与意义进行了梳理和把握。
有学者指出“五四”始终是近百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思想层面的源头活水。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并引发了关于“五四”精神文化遗产的讨论。孙先科教授认为,“五四”存在不同层面,一是主流话语中革命的、政治的、广场的“五四”,核心话语是爱国主义;二是在不同时代根据自我阐释需要而升华出来的“五四”叙事或者“五四”话语,这就是启蒙的“五四”,其以个人主义和人的解放为核心;三是上世纪80-90年代“五四”反思热潮之后出现的审美现代性的“五四”。孙教授以红色经典《青春之歌》为例,通过分析“五四话语”在红色经典中隐然可辨的诸多面向,认为已有的“五四话语”很难全面概念“五四”,研究者不能被已经形成“五四话语霸权”所笼罩,学术的姿态应该重新把“五四”历史化,还原“五四”的“真实”。孙教授也提醒,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能否在“五四”现场里边看到更鲜活的个案,它可能比我们已经触摸到的东西还要丰富得多。孙教授的发言给了“五四”研究一个新的启发,也为“五四”的叙事学分析如何应用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思考空间。
曹书文教授以家族小说的研究经验为例,指出“五四”知识分子对封建伦理的“孝”与“忠”的批判态度不同,而他们对家族的批判既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也是青年知识分子自身解放的个体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家族文化时,未能理清“家”在不同层面的文化内涵。在秩序与规范之外,“家”也蕴含了血缘情感与道德情怀以及无形的价值理想。尽管“五四”时期已经有人提出了救人比救国重要的命题,但未能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有可能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形成对人的解放的遮蔽。有学者也指出曹教授提出的家/国、理性/情感、自我/群体的几对矛盾,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均有鲜明体现,这些矛盾与问题至今仍缠绕着我们,在研究“五四”人物时,应注意对人物的思想和人格进行双重分析。
刘进才教授从语言变革角度考察“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和责任意识。他认为,与“五四”本身相比,对“五四”时期知识人的分析与思考同样重要。胡适对白话文的倡导、鲁迅的“硬译”、大众语论争、通俗语文运动等语言变革问题的持续讨论,实际上承载了一代“五四”知识分子为了建构一个统一国音、统一语法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理想,这种对语言本身的清理与反思,深刻反映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和责任意识。
在“五四”研究日趋多元化的学术语境中,研究方法的细化深入一方面的确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主流叙事造成的困扰,另一方面却又有可能陷入“化简为繁”的误区,因此“五四”的研究与阐释也成为会议讨论的另一个热点。
孟庆澍教授指出,随着学界对“五四”前史的热烈讨论,“五四”与近代的界限正在消退。他回顾了《甲寅》与《新青年》杂志的历史渊源,通过分析章士钊在民初政论文言文变革方面做出的努力,指出章士钊实践的文言文欧化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欧化,实质上采取了某种共通的知识策略,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文法的重视。他同时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以往讨论较多的语言文学,实际还包括其他路径的制度设计。孟教授对“五四”时期主流与边缘刊物的细腻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五四”时代文学生态的复杂性。解志熙教授指出,“五四”前后的社会语境有较大的差别,例如章士钊等人在清末创办《甲寅》杂志,主要面对的是政治问题,其共同思想基础是政治问题的讨论,这也造成了章士钊对文化持与胡适迥然不同的态度。他同时也指出,“五四”研究要注重具体的、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历史的大脉络、主线索。
刘涛教授在“五四”的研究方法上与孟教授持相似的观点,他强调应该重视从横向的空间角度去研究“五四”思想的发散与传播,比如考察“五四”事件的发生地北京与其他城市对“五四”的不同态度,以及“五四”在不同地域表现出的差异性影响。张先飞教授指出,“五四”研究容易陷入理论与概念的拘囿,因而对词语和概念的厘清有助于问题的讨论和深入,这也应纳入“五四”反思的重要议题。袁凯声研究员也指出,对历史现象的把握与认识,应该的逻辑是从认识论到价值论,从贴近历史到解释历史,在对历史阐释中,应对自我的认识与判断保持必要的警惕。总的来说,这些观点有助于更好地深化理解与阐释“五四”。
对“五四”的重新认识不可能脱离每一时期讨论的现实语境,因而如何重新认识“五四”也成为不同时代“五四”反思的讨论热点。解教授认为,“五四”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当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无法面对国际国内问题时,在现实危机下需要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的安排,当然也包括制度安排。“五四”运动节省了很多无谓的争论,直接将焦点聚焦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五四”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值得未来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更充分的认识,而目前我们对“五四”的认识仍然偏于简单和抽象。张宝明教授也认同在各种文化盛宴争相粉墨登场的今天,重提“五四”话题有其必要。他认为,文化自觉与自信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文化并非一切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五四”时期在某些问题的价值判断上有比较极端的倾向。张教授的观点触及了“五四”反思的另一层面,也有学者以鲁迅铁屋子的比喻为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一价值判断的标准可能有策略上的考量。
杨萌芽教授认为陈三立等在“五四”以后仍坚持古典文学阵地的创作者多具有参加现实政治的经验,从其思想构成上看,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旧文学之间并非截然二分的关系。他强调的新旧文学伴生的观点也是目前学界重新认识“五四”的一个重要议题,引起了不少与会专家的回应。袁凯声研究员认为,新旧文人面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思考的逻辑指向是共同的,即民族危亡与国家的复兴。要重视文学描绘的“五四”经验,因为在理性与知识之外,对个人经验、情感的体悟与描述往往更能凸显文学超越时代的敏感性和先导性。解教授指出,旧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如何呼应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思考内发于文学本身的新旧交融的复杂现象。关教授也认为,对新旧文学作先验的人为的区隔不符合文学研究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研究者即能把握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又能够准确把握历史过程中的大背景与主脉络。
袁凯声研究员在会议小结时指出,这次研讨会虽然以激辩和激情的话语方式讨论“五四”,实际上蕴含着严肃的态度。“五四”具有复杂的内涵指向,其复杂现象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可以认为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五四”。一是民族国家层面的“五四”。其产生于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存亡的危机与挑战;二是启蒙的“五四”,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奠定塑造了中国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并开出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五四”参与者的“五四”。不同的“五四记忆”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们对“五四”的理解;四是被阐释的“五四”。在这个层面上,“五四”真正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他提出“五四气质”问题,认为“五四气质”是由理想主义、担当精神、开放宽容、创造激情和历史缺憾等关键词组成的。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中国的发展牵动着世界,世界的发展影响着中国。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面临着新的挑战,要解决新的问题。正如讨论中关爱和教授所言,“五四”之所以成为说不完的“五四”,是因为“五四”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的文化该怎么做?我们的梦想又该如何实现?“五四”不可能提供某种确定的答案,但却有可能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去追寻,去探问。
与会专家还在拓展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共识。《中原文化研究》副主编闫德亮研究员也明确表示,《中原文化研究》乐意为这一深入拓展的研究提供阵地。(孟舜)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